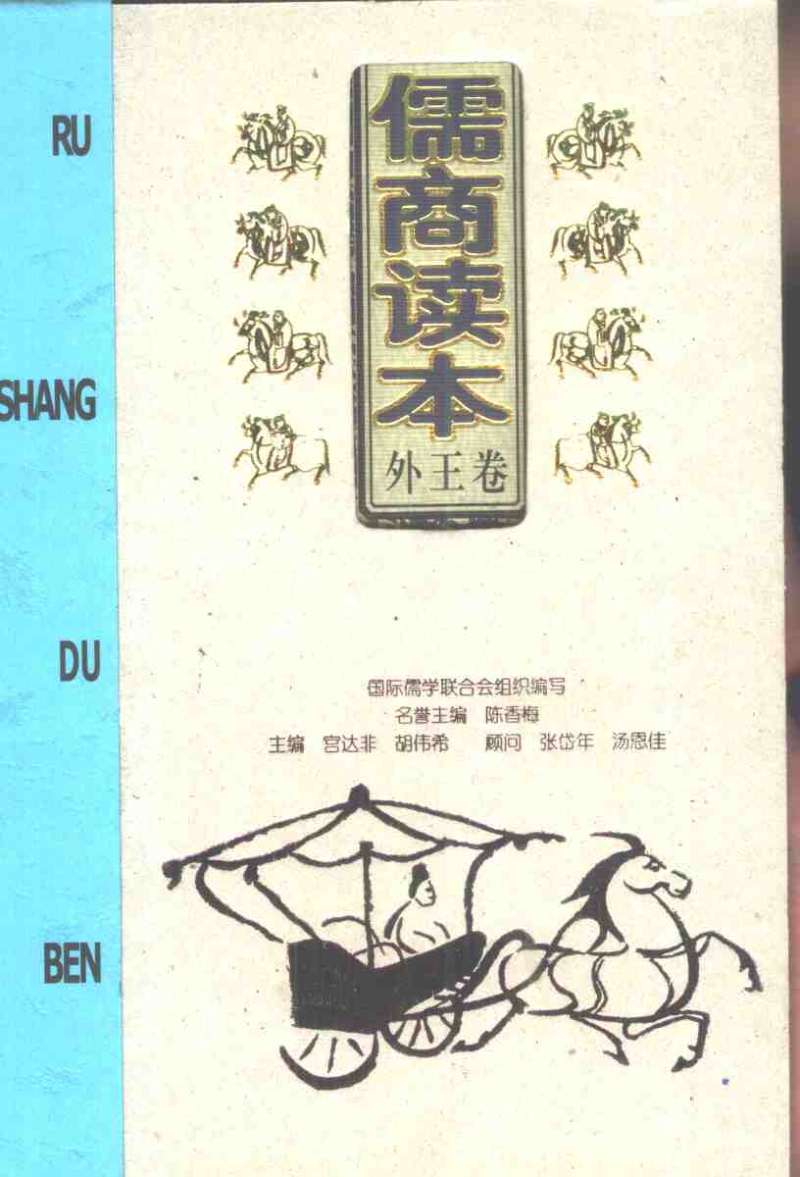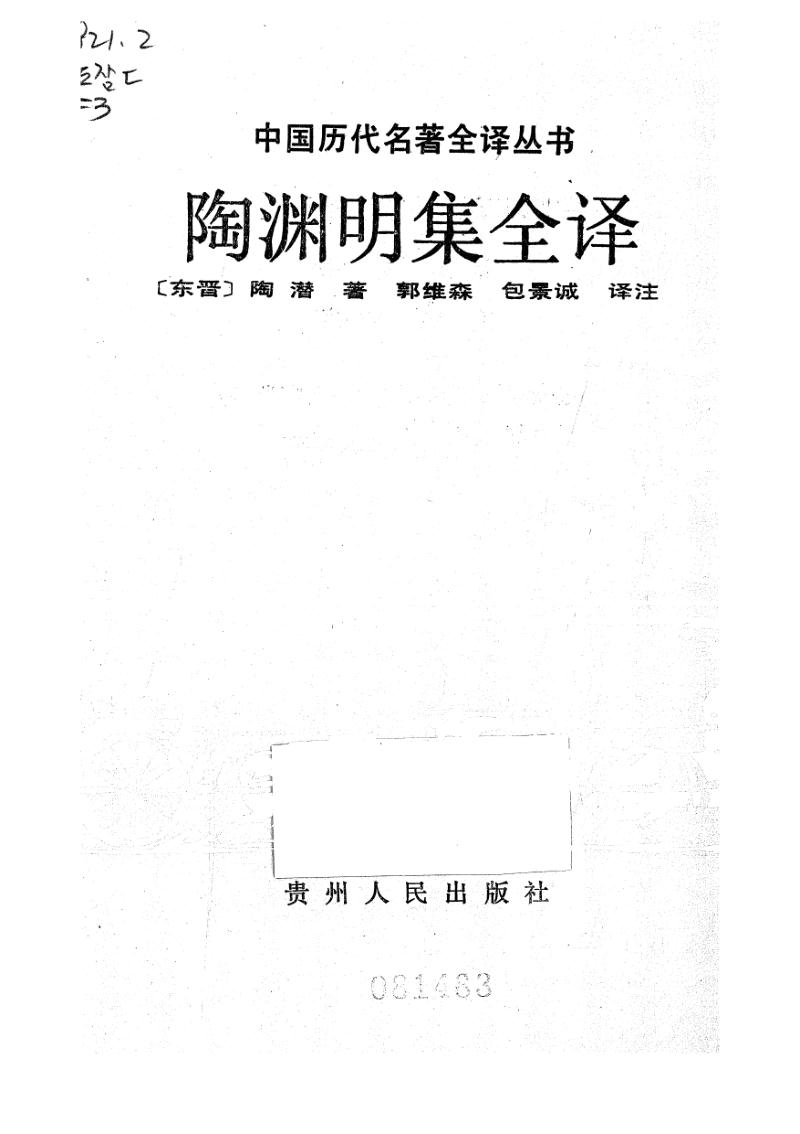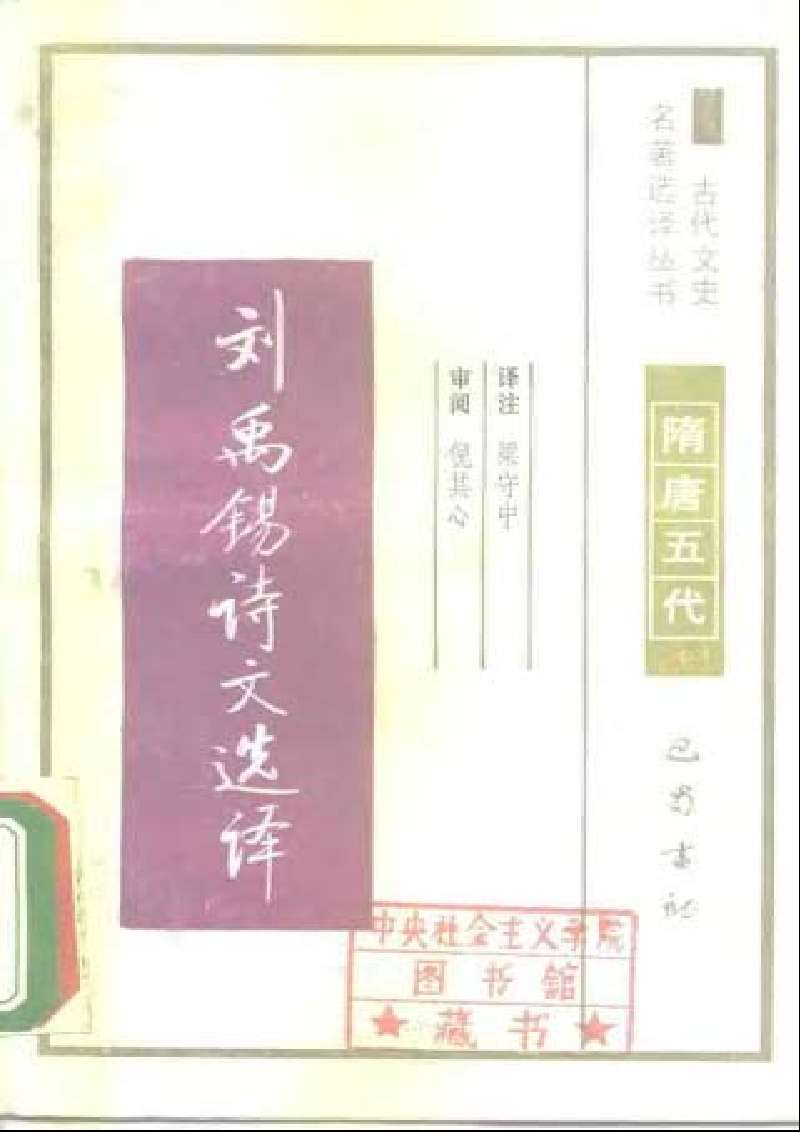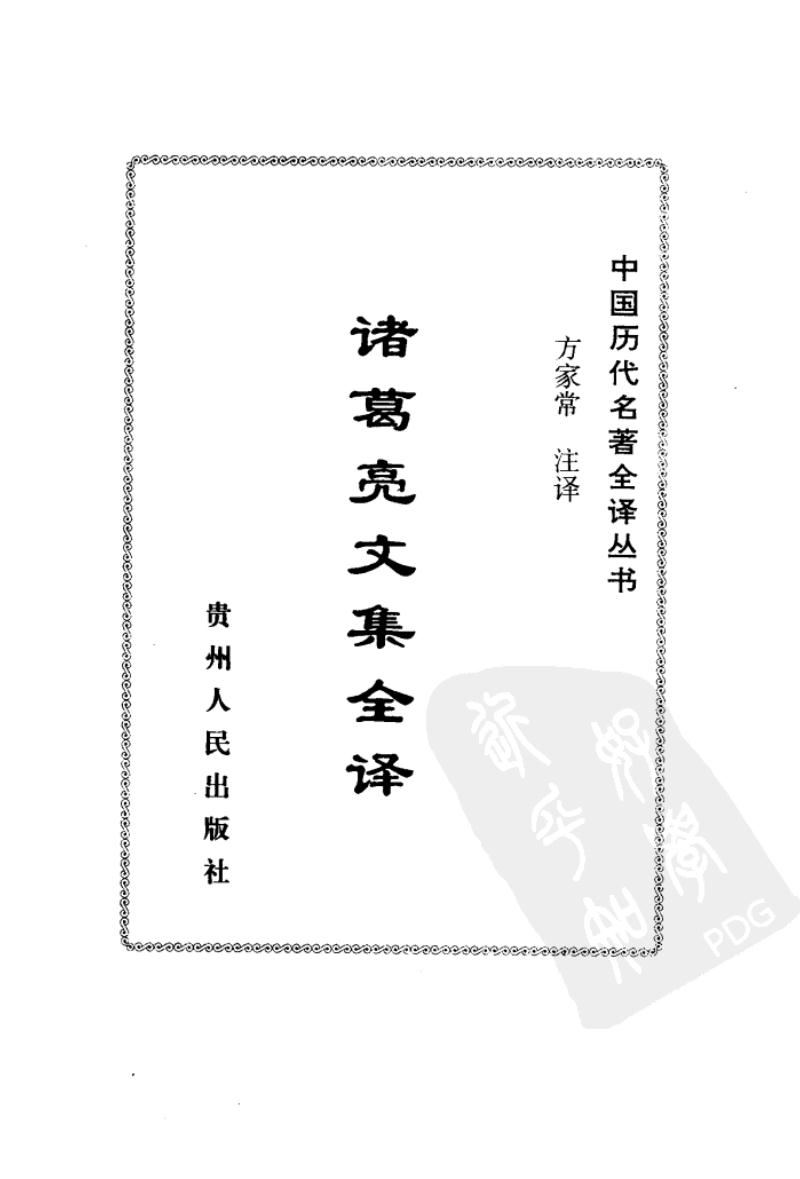许氏宗衡者,楚人也,乙未生,其字未详,传临盆之际,有万千蝗虫附于田野,乡民未知其故,县令怪之,遂记于志。
及长,游学乡邻,其智甚大,时逢政局混乱。学毕,差于南岳之农场,立为长。其文才韬略,少年老成,同侪望之莫及,有识者阴人曰,此非池中之物,日后必成大器,期年,交通官曙独识其才,招而训之。又二年,事于车马技术事,其技术精湛令前辈叹为观止。若如此,不过技工而已,然此皆非许之愿也。
时有机缘,衡南某官巡视,恰遇许之技术表演,惊。又识其貌,自曰:“此大才之人,屈居一隅,乃天耗英才”,旋提之,委以行政之职。且私对其语曰:“衡南成大器者,必在汝也,老朽已无可为,独以家人托之”,许感其恩。
文革后,许终谋高职,为中共某党组织之长,政令一郡,何其威也,然,其心志抱负又岂是一郡可矣?
廿年期整,鹏城人事有缺,皇室有识许之才者,荐之。然位置之低不可与衡南之职相比,人或有劝其言曰,“此迁,有贬折之意,不可”,许氏笑曰:“井蛙岂知海之大哉,海黾又知宇宙之无穷也,独守一隅,虽位极人臣,又能何极?吾少时且志在四方,今新职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,然岂知易之变也,此风云际会,方可显我英雄本色”,急迁之。
初涉鹏城,许便暗自盟誓,以清廉为本,不留遗憾,亦无骂名。许以一偏隅而弄大潮,自呛水而不知所措,沉十余载而未得迁升之道,每明月清风之夜,顾影而自怜,叹怀才而不遇,一日,同僚有华诞者,其排场之阔,宾朋之多,令许自叹弗如,哗然散席,许对镜抚发而言曰,入宝山而空返,况入天命之年,无奈建树何在焉?其妻慰之,“仿效某人,可飞黄而腾达哉”。许忿然以对,曰:“汝愿吾为天下笑耳?勿复言”。
至乙酉年岁终,其有黄氏高官入主粤府,许以其廉洁之本,铁腕之才调弄鹏城之长。其上任之际,大刀阔斧,兴利除弊,兴土木,造桃源,建地铁,办大运,商香港,帮莞惠,东西通达,南北畅顺,其何壮哉。市民咸曰,许真乃国之栋梁,百年一遇。
然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昔孔子曰,“季氏之祸,在萧墙之内”,待东窗事发,夫妇被拘,方如梦初醒,然为时已晚,许回首往事,自惭无及,遂思一死以谢天下,吞筷未果。
吾视此等脏事久也,然许之事令人痛心何及,清廉之士落马,盖无能避亲交美人而已矣。其妻贪之,美人索之,陷此万劫不复之门,岂能自保哉?



 节日游玩 能不慎乎
节日游玩 能不慎乎 摸霍去病雕像祈盼健康
摸霍去病雕像祈盼健康 虎兔生肖交接
虎兔生肖交接 壬寅(二零二二)爱文言年度汉字:封
壬寅(二零二二)爱文言年度汉字: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