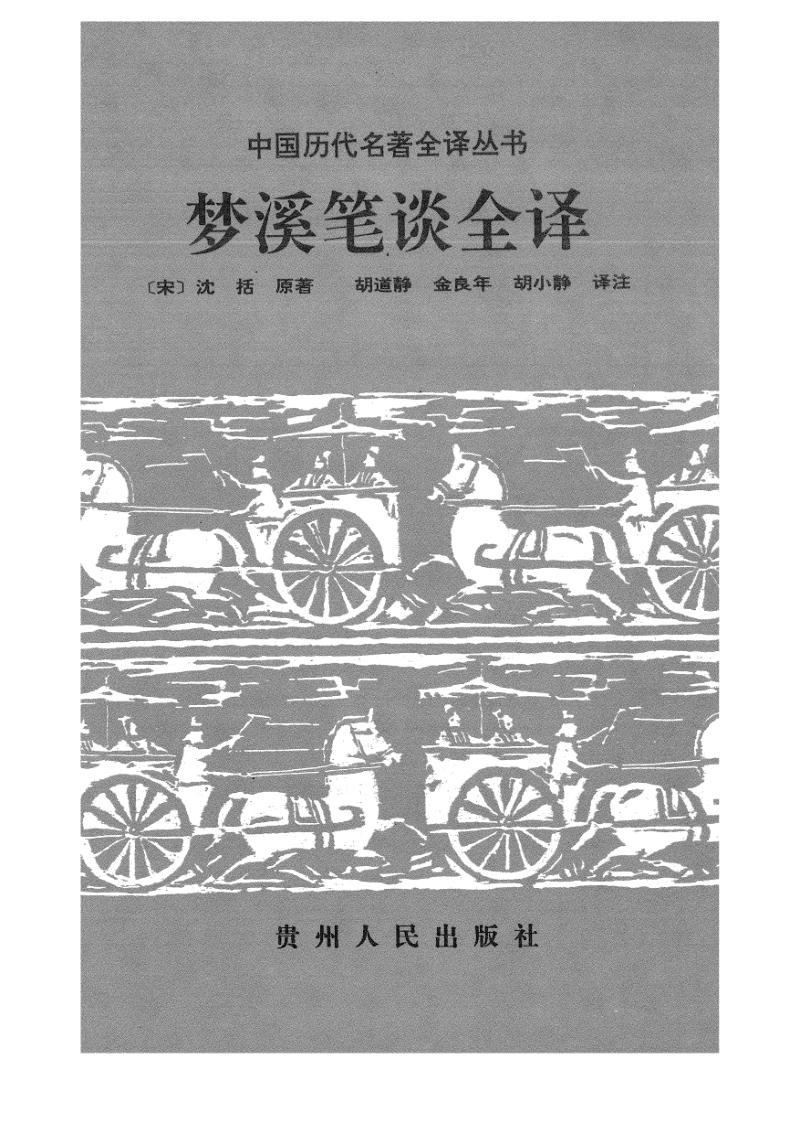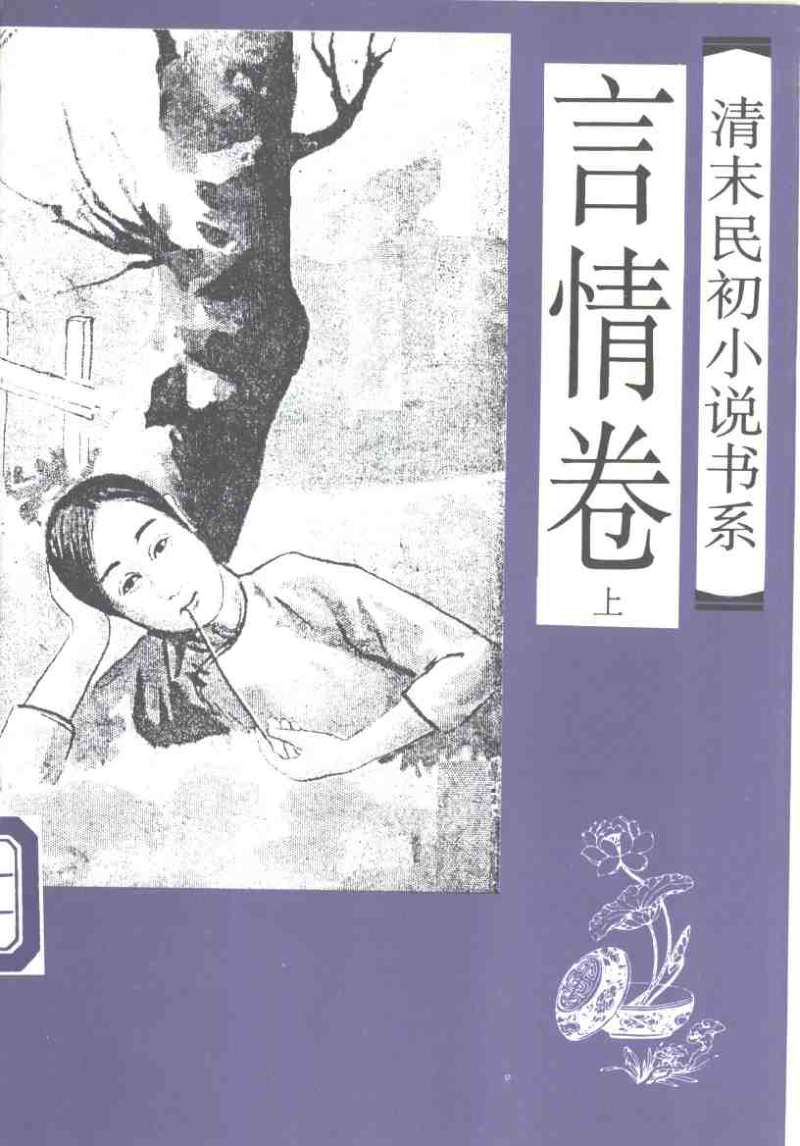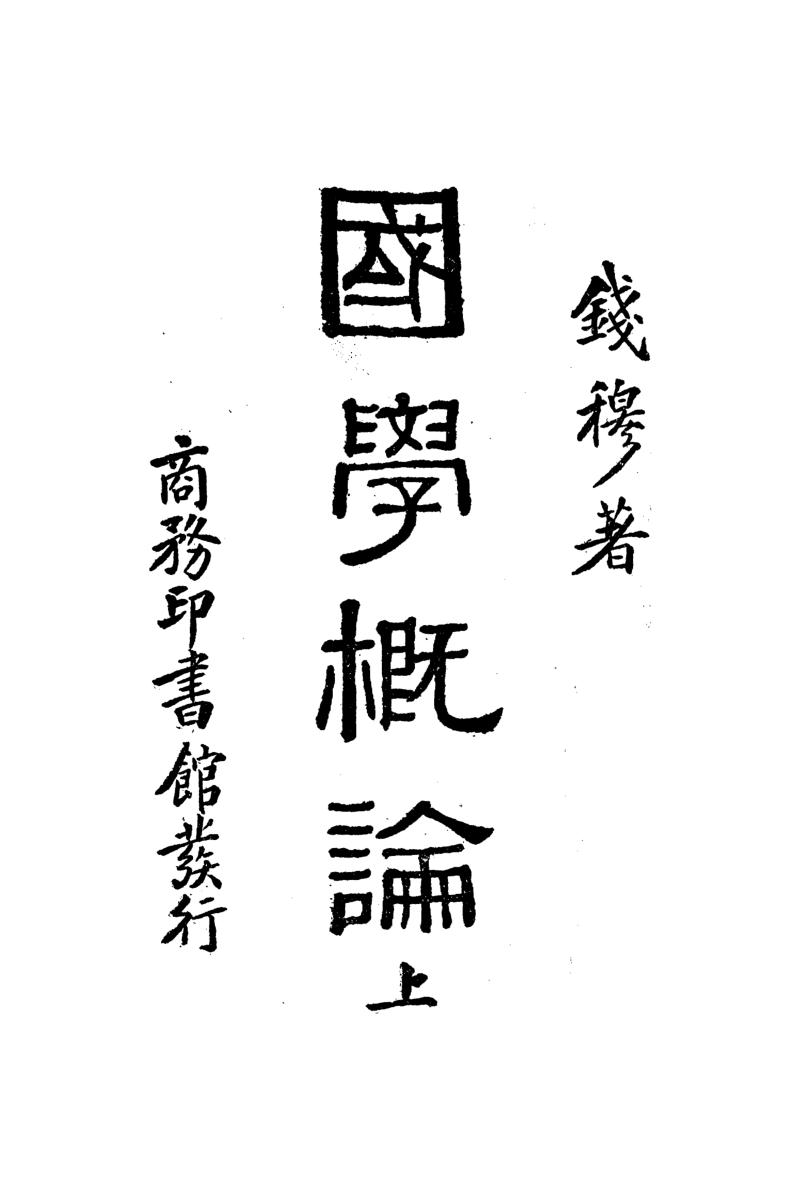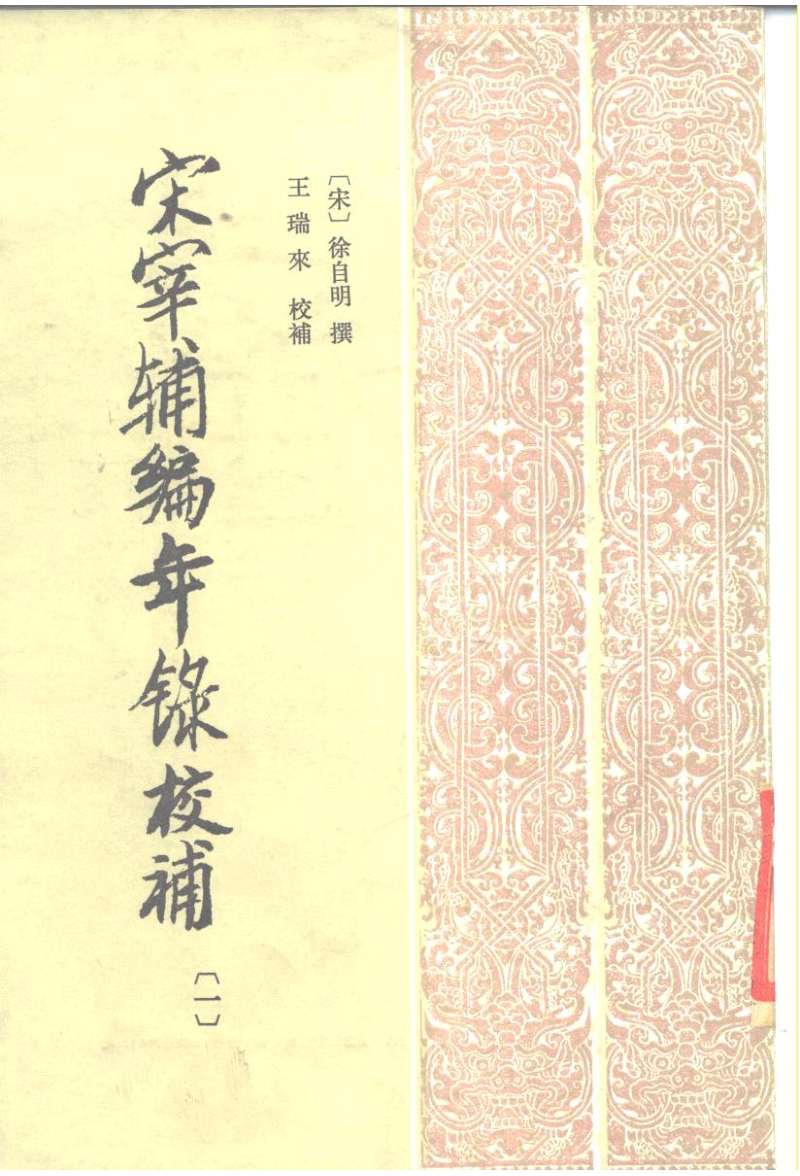酒者,谷物之酵酿也,其存于中国久矣,源远流长,夏之仪狄始作酒醪,变五味,殷之杜康作秣酒,是说也,人皆信之。昔者,酒乃民之所必需也,不论皇室贵胄抑或贩夫走卒皆莫能离,骚人墨客尤甚。古之诗赋与酒相交者何其多也,亦使得酒诗自成之文人甚蕃,曹孟德之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李太白之“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复醒”,杜子美之“醉里从为客,诗成觉有神”,及苏东坡之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此例俯拾皆是也,如是,酒之为德久矣。古人甚爱饮酒,何也?一则寄情于酒、借酒消愁者,有如李太白之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,二则风流倜傥、狂放不羁之士,刘伶之《酒德颂》有云:“有大人先生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期为须臾,日月有扃牖,八荒为庭衢。幕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兀然而醉,豁然而醒,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孰视睹山岳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。其“至人”之境无人能及也。夏禹曰: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,安此言能阻后人之恋酒邪?由是观之,时人爱酒非口腹之好也,盖情趣所寄,希求庄周之游乎四海之外,了却生死利禄之羁绊。然至今时,醉翁之意不在酒矣!饮者可见于群宴,觥筹交错,势迫也,非其志也,而酒亦成谋利之器,悖其旨,民惧之,弗受。是日,国之人大修律,是将“醉驾”载入刑律以为制裁,如此状,民之视酒为洪水猛兽矣。嗟夫!今人与古人之于酒何其异也,何哉?非酒之过也,酒亦当初,然世风及人心有变。较于古人,今人之淳朴与洒脱有缺,浮躁与功利有增,酒之所载亦重,今酒与人之欲望、贪婪乃至阴谋相勾连,独不见昔时之快意。民之饮酒,究其初衷,远非今世可比,盖此酒非彼酒矣,酒之所寄者消散于酒精已矣,踪迹不觅。
翻译:
酒是由谷物发酵酿造而成,其在中国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夏朝的仪狄最开始造酒醪,生成五味,殷商的杜康造秣酒,对于这种流传,人们都相信。自古以来酒就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,无论是皇家贵胄还是贩夫走卒都离不开,对于文人墨客而言,酒尤为重要。历史上多少的壮丽诗篇都和酒有关,多少文人是在酒中寻找到创作灵感的,曹孟德的“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”,李白的“钟鼓馔玉不足贵,但愿长醉不复醒”,杜甫的“醉里从为客,诗成觉有神”,还有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,正是这样,酒作为德行已经很久了。古时文人为什么喜欢饮酒呢?有的是寄情于酒、借酒消愁,例如李白的“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消愁愁更愁”,有的则是为了展现出风流倜傥,狂放不羁,刘伶在《酒德颂》中有言:“有大人先生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期为须臾,日月有扃牖,八荒为庭衢。” “幕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”“兀然而醉,豁然而醒,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孰视睹山岳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。这种“至人”的境界是常人无法相比的。断使夏禹有言: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,难道这一句话就能阻止人们对酒的沉迷吗?看来古人对于酒的喜爱已不仅仅是口腹之好了,更是情趣、寄托所在,通过酒来追求绝对自由、 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的束缚。然而现在人们对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,如今人们饮酒一般是在正式的宴席上,很少是因为兴致,更多是迫于形势,不得不饮,酒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谋利工具,基本上丧失了它本来的意味,人们也渐渐对酒产生了恐惧与排斥,成为人们的负担,不再有使人洒脱的功效。不久之前,全国人大立法,将“醉驾”编入刑法制裁,看来现在的人已将酒视为洪水猛兽了。唉,今人与古人对于酒的态度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,为什么会这样呢?这并不是酒本身的过错,酒还是当初一样的酒,而只是世风和人心发生了改变,现代的人少了些许千年前古人的淳朴与洒脱,多了些浮躁与功利,酒所承载的东西也就较之前更多了,如今酒跟人们的欲望、贪婪乃至阴谋相串联,唯独不见了当初的那份快意。从人们饮酒的初衷来看,今人和古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,因为这酒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酒了,那份寄托和情趣在酒精中消散的无影无踪了。
作者:xiaoluoyun1234



 谢林君谏果启
谢林君谏果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