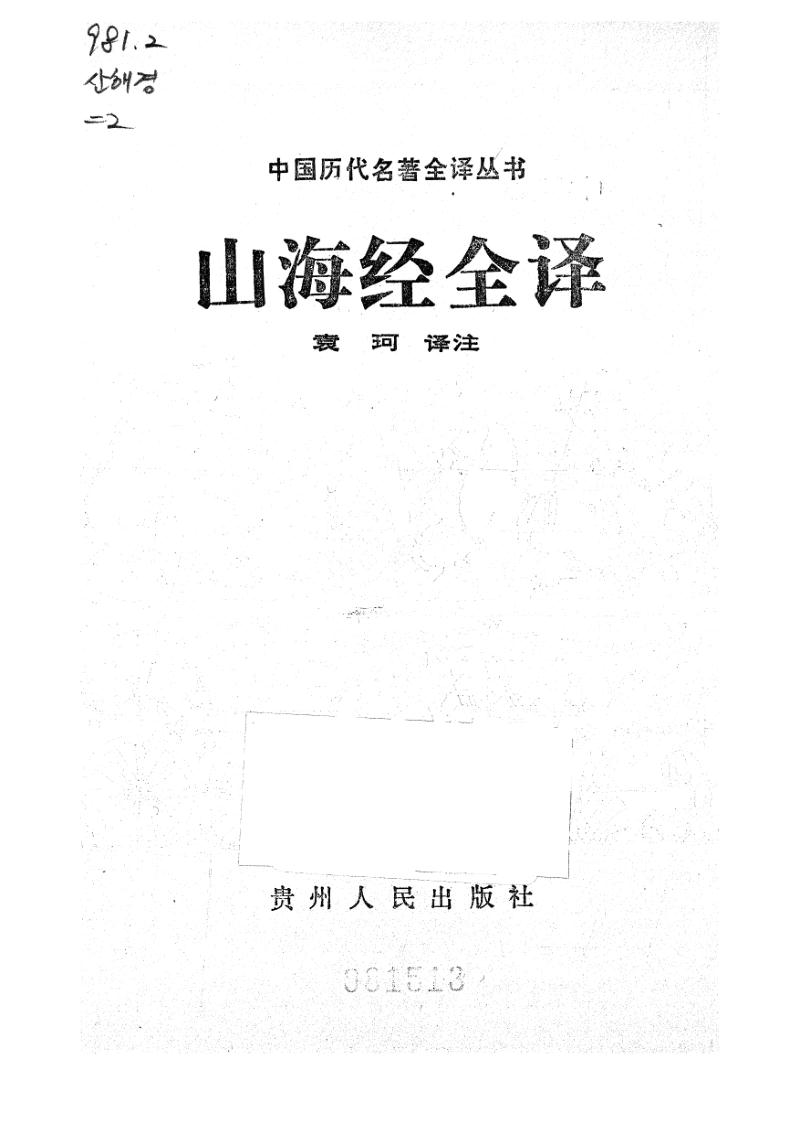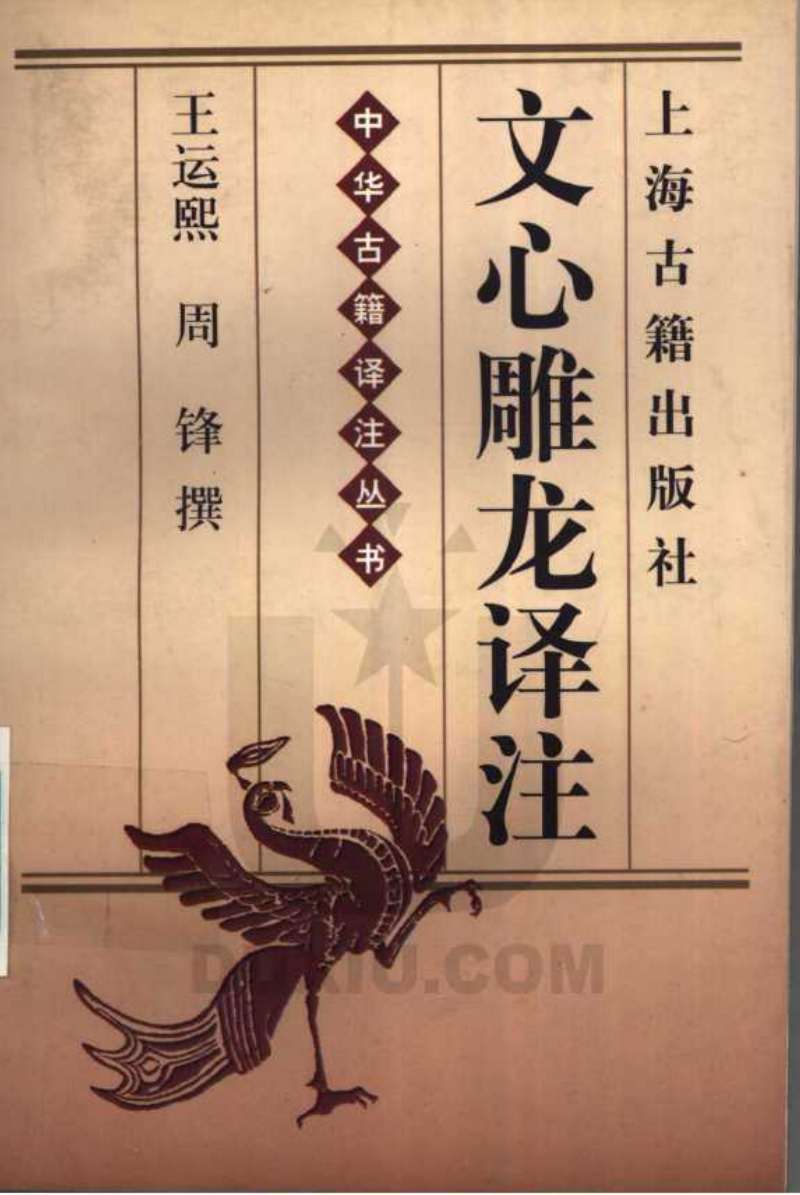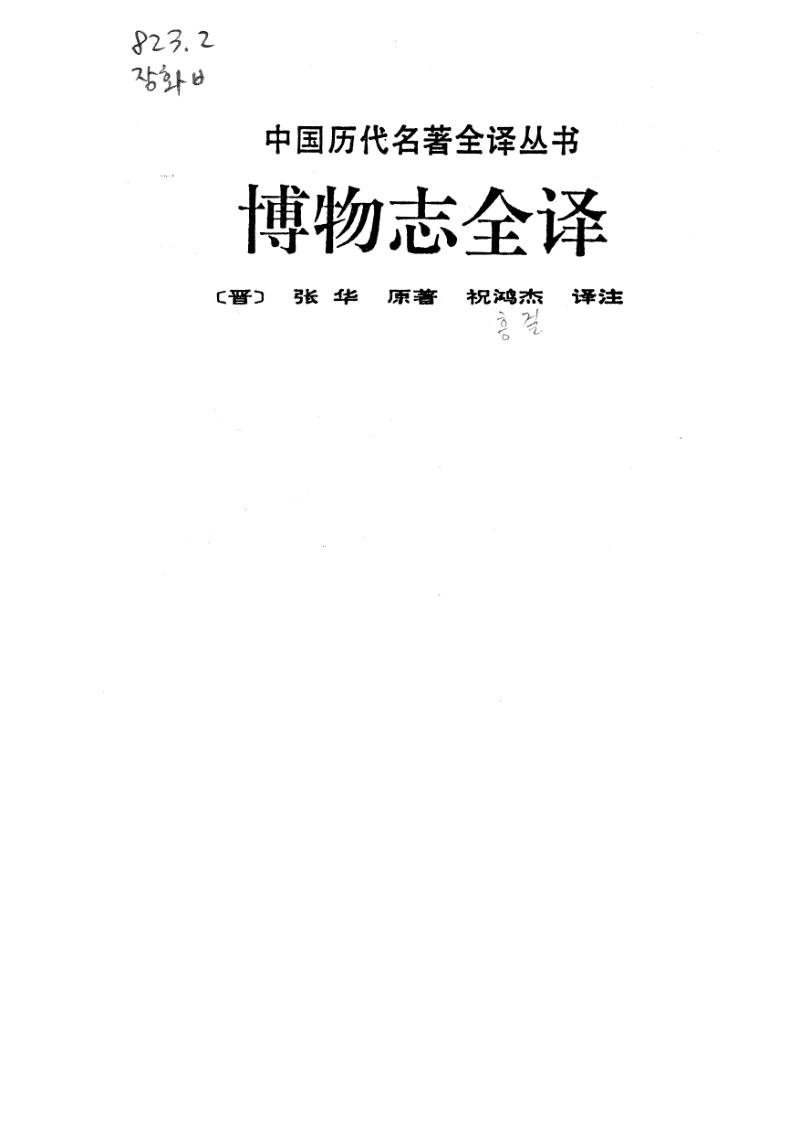郭公讳沫若,蜀中乐山人也。初名开贞,后自改之。父朝沛,乐山贾人也。家殷实,无虑饥寒。沫若幼聪敏,诸学无不通。年十一,即能诗,蔚然可观。其诗尝曰:高格自矜赏,何须蜂蝶谀。乡人以为神童。沫若少有才名,人皆不及。
年十六,游学成都,性甚疏狂。时聚朋类,白日纵酒,信口吟章,亦以狂生闻。年二一,涉东瀛。尝恋倭女佐藤氏,呼为“安娜”,与同居焉。沫若素喜西学,博极群书,宏然大观。
年二七,得《凤凰涅盘》,时以为嘉。年二八,辑诗集,曰《女神》,名遂轰然。
沫若与郁达夫、田寿昌善,相约回沪,结创造社,行杂志文艺。周年,社废。佐藤氏携子去。沫若甚苦焉,遂信马列。
北伐起,沫若从戎,授参军。民国四年,授广东中山劝学司。南昌之变,沫若中途随军,始入共产党。武厉帝疾之,缉焉。沫若亡入东瀛,研甲骨文,著述颇丰。倭军侵华,沫若归国。著《战声集》。传檄天下,振呼抗日。沪淞之败,沫若身赴武汉。长沙陷,赴重庆。皖南之变,国人谴之。沫若作杂剧《屈原》,褒屈子之高洁,诟宋玉之无行。一时争相传焉。倭寇降,内战复起。沫若乃集会党人,呼吁民主。国民党禁之甚严。
民国二十七年,沫若身赴莫斯科。无何,归,途歌“于今北国成灵琐,从此中华绝帝王”;诣太祖,复歌“ 以吾皇之意见为意见”。遂宠于太祖。
建国元年,使于布拉格。我朝初开,授以翰林院编修、国子监祭酒、礼部右侍郎。沫若常侍太祖左右,甚得帝心。言必以阶级,歌必以太祖思想。常以人前高颂太祖诗词,以为荣耀。时反胡风,则诟胡风;时倡跃进,则歌跃进。是以仕途亨通,一时无双。然其文华诗词,与其少时,判若两人矣。时人皆畏而耻之,以为弄臣。太祖尝御书一联,误书讹字。帝本不以为意,沫若辄曰:“此即吾皇革命之豪情也。”太祖文不以标点,沫若辄曰:“此即吾皇不羁之明证也。”呜呼,幼笑蜂蝶之谀、长慕凤凰浴火者,一朝庙堂,奈何谄佞至斯哉!
文革起,沫若甚惶恐,乃思自焚其文稿以避祸。方数月,表忠心颂文革数焉。然祸犹加之,二子死于红祸,至周文正公护持,祸始稍弭。
沫若初党林彪,彪窜死,则媚江后。尝于万人前曰:“吾以陋诗献圣母皇后。”丧爱子而不敢痛,犹摇尾于凶徒之前,以今日量之,亦可怜矣。太祖崩,文革罢,江后之党幽闭。沫若乃诗以“还有精生白骨,自比则天武后,铁帚扫而光。”人多耻其反复,言辄唾之。
改革元年,卒于京。谥为“文丑”。以其章奇藻丽,故曰文;以其谄佞无行,故曰丑。论曰:沫若少有才名,博学多闻。观其诗文,实乃大家。奈何以李、苏之才具,蹈贾、和之行径!其尝曰宋玉“无耻文人”,由今观之,岂独宋玉无耻哉?!先哲尝曰:文人当远政治。以沫若观之,信夫!


 节日游玩 能不慎乎
节日游玩 能不慎乎 摸霍去病雕像祈盼健康
摸霍去病雕像祈盼健康 虎兔生肖交接
虎兔生肖交接 壬寅(二零二二)爱文言年度汉字:封
壬寅(二零二二)爱文言年度汉字:封 羽毛球之窃场轶事
羽毛球之窃场轶事 钢铁侠传
钢铁侠传